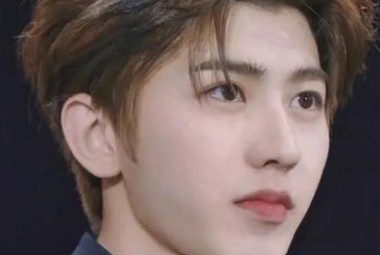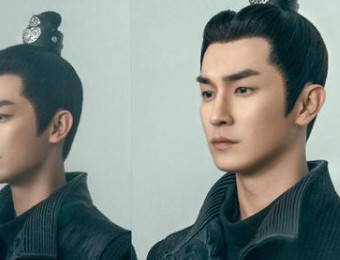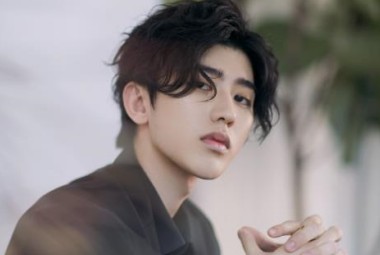這是《好奇心日報》與《虹膜》電影雜志合作的「電影與城市」系列,每周末更新。
全世界幾乎沒有哪個地方像香港一樣被電影表現得那么徹底,香港和電影,這兩個詞有時候更像是硬幣的正反面,已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僅僅通過觀察香港電影從戰后直到今天的發展變化,某種程度上就等同于看一部活生生的香港城市變遷史,其中不單有城市化和現代化對市民階層的影響,更體現著本土文化發育深化的過程。
讓人驚嘆的是,我們幾乎可以在任何類型片中見到這座城市的蹤跡,這就是香港電影獨特的魅力所在。如今香港電影式微,你可能已經不再關注和它有關的作品,但總有一些電影讓人難忘。
《歲月神偷》
《歲月神偷》是一出典型的帶有香港本土自覺的懷舊文藝片,一如「新浪潮」及其之后出現的一批既有「香港經驗」又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導演,羅啟銳和張婉婷一直以來也在電影中回望著香港的過去,并通過影像加強著這一種地域的認同感。兩位導演在這部影片中延續著以往的創作風格,選用非常有傳統有認同感的「家」的流轉來映襯香港與香港人的關系,其中除了溫和的人倫常情,親屬關系和歸屬感,更有諸多能代表城市文化和歷史印記的標識。
永利街是香港上環的一條小街道,由于沒有車道,必須沿著樓梯走才能到達,雖然狹小,但卻成為香港這座都市中少有的遠離高樓大廈和城市喧囂的一隅,也被認為是時下香港唯一一處保留六十年代特色的地方。不僅如此,這條街上更有12座由青磚砌成的「唐樓」,這種建筑的一層通常作為商鋪,樓上則用作居住,是現如今整個香港都難尋的帶有歷史風味的建筑。《歲月神偷》便主要在永利街取景,于是古老而滄桑的街道在大銀幕上煥發出新的色彩,某種程度上,《歲月神偷》甚至就是為保存永利街文化風貌而存在的一部影片。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樣一處實景的話,影片的訴求會怎樣的大打折扣,而永利街在飛速的城市發展中又有可能遭受怎樣的劫難。
《人間·小團圓》
提到香港電影與城市,彭浩翔是繞不過去的一個人。即使「北上」之后,彭浩翔的作品開始較多涉及香港之外的城市景觀,但「香港」作為他電影甚至他本人的精神內核,卻持續地為其提供了創作的素材和靈感。《人間·小團圓》就是在內地上映卻表現彭浩翔的香港情結的影片,在《春嬌與志明》和《低俗喜劇》之后,本片的上映尤其有趣,某種程度上,也正因為這部影片在內地的某種「失敗」,才有了之后更加抹去作者標簽的《撒嬌女人最好命》。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人間·小團圓》中一窺彭浩翔創作的變化過程。
《人間·小團圓》和彭氏前作最大的不同,也許是人的狀態和家庭觀念上的,事實上,它講的是一種價值回歸。婚姻危機、事業瓶頸、父子關系都成為現代香港普通家庭瓦解的象征,但是在影片中,也許是人物和線索過多的原因,彭浩翔讓這些問題在影片中想象性的得到解決,而有意無意地回避了某些深層次的問題。然而,和彭浩翔一貫擅長的劇作相比,這部影片在思考香港的城市問題卻走得比較遠,某種程度上,擱淺的鯨魚正是香港的暗喻,眾人對鯨魚的「拯救」也帶有了一絲對本土意識的喚起。而在楊千嬅夢境的一段,香港更是被演繹成一種平面化的微觀城市,加上歷史遺留炸彈和環境恐慌,都成為籠罩于城市之上的陰云,也給影片制造了觀察香港這座城市的別樣視角。
《僵尸》
2013年香港電影的最大驚喜恐怕要算麥浚龍的《僵尸》了,一方面可能是太久沒看到香港出產如此純粹的僵尸片了,另一方面則要歸結于影片既凸顯出新意、技術和對美式、日式風格的借鑒,又對香港本土電影有所回歸和指向,讓人依稀看到香港僵尸片在最鼎盛時期的元素,這無論對于香港還是香港電影來說,都是一次致敬。
在緊扣「僵尸片」這一類型的前提下,麥浚龍將影片空間設置于香港一棟破敗老舊的公寓,這本身與影片想要制造的陰森氛圍非常合拍,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老式住宅也凸顯著其中居民的「老」。在片中悉數登場的香港電影的老面孔就像這座無人問津老樓,塵封自己的過往。作為導演處女作,《僵尸》無疑是具有才華的,麥浚龍不但對封閉空間內的氣氛和年代感把握較好,更對時間有著獨特的領悟,后者當然涉及到情懷了。看到最后,你會發現電影最后歸結到逝去的和被遺忘的人,錢小豪事業的低谷也正是香港電影最輝煌歷史一去不復返的寫照,既有懷有更有傷感,于是影片的層次也一下子被提升了不止一個檔次。從這一點上看,《僵尸》的表述非常「香港化」,就像片中照片上的林正英,依然代表著人們心中的那些值得追憶的香港電影。
《籠民》
在1990年代的香港影壇,《籠民》絕對是一個另類。這一時期香港電影開始經歷從「黃金時代」的浮華逐漸降溫的過程,而電影也回應著這種變化。即使依舊表現其與城市之間親密的互動關系,《籠民》中已全然不見《最佳拍檔》中的摩天大樓和現代飛行器,也沒有半點許冠文電影中表現出的「造城」景象和市井文化空間,而是將目光聚集于一棟棟樓房的內部,對城市不為人知的角落和最底層市民的生活狀態做了一次社會學式的考察。
《籠民》中的人們棲居于一棟危樓之中,鐵絲網把本來不大的空間分隔為一個個鐵籠,而這些鐵籠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場所。然而,僅僅是這樣的住所也難以保全,拆遷的腳步還是來到了這個籠屋群落中,在居民們齊心對抗強拆的過程中,影片又一次涉及到腐敗的議員、媒體的反思等社會議題。于是,在這部帶有強烈寫實色彩和現實批判的另類的香港電影中,籠屋群落逼仄的空間成為城市的一種注腳,我們也得以從滿眼的類型片中看一看香港城市空間中不為人知的真實的另一面。與影片寫實主義的基調相吻合,張之亮用了大量的長鏡頭來拍攝「籠屋」,于是封閉狹小的空間得以在流暢的鏡頭中完整呈現,而生活于「籠屋」中的民眾可謂在小空間中盡顯人生百態,出色的人物群像塑造更加深入的闡明了城市發展對社會底層市民生活的影響。
《重慶森林》
與那些致力于在電影中呈現香港的在地化特征相比,王家衛卻更注意那些混雜或異質的部分,這基本上也構成了他電影風格的核心部分。在《重慶森林》之前,他拍攝了由劉偉強擔任攝影的《旺角卡門》,同樣是以香港的城市地標為故事展開的重要場所,后者更像當時普遍存在的港產電影,通過旺角一地抒寫香港人的故事。然而,從《阿飛正傳》開始,香港不再是劇中人心靈的歸屬,而遙遠的異域他鄉成了他們要追尋的過往,無論是《阿飛正傳》中的南洋還是《春光乍泄》中的臺北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都是主人公離開香港去獲得身份認同的地方。與此相比,《重慶森林》沒有讓主人公遠走,而是選取了香港城中的多元文化聚集地,去表達這種文化的特異性和豐富性,以及由此而產生人們之間的疏離。重慶大廈是位于香港尖沙咀的一座高樓,其中擁有多個廉價賓館、商鋪及飯店,更是居住了大量的少數族裔人士,其中以印度和巴基斯坦和非洲國家的人士最多,被稱為「香港少數族裔的九龍城寨」。這一國際化的地標在《重慶森林》中成為一個核心的概念,在槍殺和販毒的故事起點下,王家衛實際上強調了這一文化空間和人們孤獨狀態的同構,在這里,一切是碎片化的,愛情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傷感才是永恒的。
《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作為系列第一部,現在看來有著非常復雜的意義,它不僅是《煎餅俠》中用來勾起集體回憶的文化要素,更代表著香港黑社會電影既傳統又有活力的一種,以及 1990 年代香港電影在凋敝的景象中求生求變所作的努力。王晶、劉偉強和文雋的組合賦予了這個系列電影全新的文化意義,雖然粗糙但卻生機盎然。
作為系列的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為之后的續集和番外篇設定了所有的要素,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人物和他們的生存場所以及生存方式,片中,人物已經和香港的城市空間融為一體,無法分離了。從城市地標上說,《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基本上由人物屬性就劃定了香港的城市地圖,如陳浩南掌管的銅鑼灣,山雞掌管的屯門,之后的續集中更是有大飛哥掌管的北角和十三妹掌管的砵蘭街等。
這些屬于城市的特色,同時又亞文化生機滿滿的地帶為影片增添了濃重的時代感和生活氣息,而在這些地帶的呈現上,劉偉強也大量的采用手持攝影來拍攝,這一原本是出于預算緊張而實施的方案反而在這樣的電影中富有了新的審美意味。搖晃的鏡頭下香港街頭的燈紅酒綠凈收眼底,而在街頭行走的古惑仔們也與搖晃的城市背景融為一體,這其中,或時尚、或叛逆、或熱血,一切都交給觀眾自己了。
《金雞》
趙良駿眼中的香港與其他香港導演似乎有所不同,他所理解的香港好像沒有那么多血雨腥風,浮華景象,也很難看到對于社會現象無情的揭露、辛辣的諷刺或者難堪的隱喻,反而多有了一份人情味和對以往生活的追憶,體現的是城市的變遷對人的生活以及情感歸宿的影響。這種傾向早在《記得香蕉成熟時》便有所體現,而兩部《金雞》之后的《老港正傳》則反映他想要進一步追憶的某種矯枉過正。
《金雞》以及《金雞2》是呈現香港社會變遷的典型作品,在妓女阿金一生的追憶中,香港也將其走過的路進行細數,行業的變化、政治事件的影響、人物的命運都緊緊的交織在香港這座城市之中,不禁讓人唏噓感嘆。除此之外,影片最成功之處莫過于塑造了阿金這一形象,她一生艱難,但卻不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她歷經世事,但依然努力向前。某種程度上,阿金代表的正是香港人刻苦耐勞,又積極樂觀的香港精神,正如《獅子山下》和《一生何求》所唱的,香港這座城市也在不斷進取不斷拼搏,并且一直相信奇跡的存在。由此,影片傳達出的價值觀便十分明顯,即使有那么一點老套,但畢竟,通過與城市共生的命運來增強民眾的自豪感與凝聚力確實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天水圍的日與夜》
許鞍華曾先后拍攝兩部有關「天水圍」的影片,一部平淡一部激烈,表現的恰好是「天水圍」這一城市地標的兩面。天水圍位于香港新界的元朗區,本是經過改造開發而形成的住宅區,卻因為其「悲情新市鎮」的叫法而具有不一樣的社會文化意義。
2000年以后,這里人口急劇上升,尤其是公屋中大量由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新移民的入住,使得這一新市鎮具有了與傳統意義上香港在地文化不一樣的特征,加之陸續出現的幾樁倫常慘劇,更加重了人們對天水圍獵奇認知。許鞍華在《天水圍的夜與霧》中就直接描述了發生在一個大陸移民女性家中的慘案,然而這一似乎取材于真實事件的故事卻沒有收到比平淡的《天水圍的日與夜》「更真實」的評價。在《天水圍的日與夜》中,脫離了奇觀化的天水圍與其他的社區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鮑起靜飾演的阿貴和陳麗云飾演的阿婆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由陌生人變得熟悉與靠近,兩個殘缺的家庭也完成了想象上的重組。顯然,對于這個具有太多沖突與分裂的社區,許鞍華至少在這部影片中強調的是和解,是冰冷的現代城市中人們之間僅存的一點溫暖。天水圍普通的日日夜夜回歸到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被情感和傳統文化所聯結的關系,影片尤其強調飲食,榴蓮、月餅、花菇等食物,這背后則是割不斷的人倫常情。
《文雀》
杜琪峰的電影一直離不開城市空間,在他的鏡頭下,香港仿佛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既是人們庸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諸多犯罪、槍戰的上演地。某種程度上,我們之所以認為《黑社會》是寫實的,大概是由于它描述出了這種城市中的庸常生活,而我們又認為杜琪峰的電影是有「港味」的,可能是這因為深深嵌入電影中的只屬于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間吧。與前作相比,《文雀》是一出精美的小品,在極簡的故事和突出的配樂下,影片將人物放置于香港城市的街頭,展現了別樣的從容。在影片前半段,與其說杜琪峰是在拍「偷」,不如說他是在拍「城」,流動感極強的鏡頭跟隨四位主人公走遍香港的大街小巷,于是茶餐廳、寫字樓、巴士站成了影片表現的主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任達華飾演的四名職業扒手的首領「祺」閑來騎著自行車拍攝香港的街頭景象,當普通的香港市民連同不加修飾的市井形象一同定格于杜琪峰的鏡頭之中時,影片也就暫時拋開了故事而呈現出更濃厚的文化氛圍。除了寫實,《文雀》中的香港又是寫意的,屋頂、樓道和狹小的電梯間映襯著游戲化的人物關系,雨夜的一場又將杜氏電影的浪漫氣質發揮到極致,其實,《文雀》本來就在說人的生存狀態,他們已經成為香港的一部分,在這座城市不斷的讓故事上演又不斷的讓其悄然結束。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陳果的創作序列一直與「香港」或「九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無論是《香港制造》中的居民住宅、《細路祥》中的茶樓,還是《香港有個荷里活》中的大磡村,都通過對獨具特色的城市角落的描述呈現出了人與城的關系,在濃重的本土風味背后,則是「九七」臨近的時代癥候。可以說,人、城、時代,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關系一直是陳果早期作品關注的內容與現象。在幾部恐怖片之后,陳果終于推出這部十分復雜的甚至連片名都十分拗口的影片,片中表達人與城市的關系上與前作一脈相承,但卻走的更遠。一輛小巴車聯結了香港的九龍旺角和新界大埔,一群身份各異的人也隨著這輛小巴車在一夜之中穿過這條線路,同時也進入到了一個完全隱喻化的香港中。在這兩個城市地標之間,陳果呈現出香港的末日景象,同時又表達出強烈的對以往時光的追憶。影片結尾處,當鏡頭俯瞰過香港上空,銀幕上出現了「隨著這座城市暗光沉睡之時,我們有否已淡忘了曾經光輝的過去,不知今夕何夕」的字樣,陳果的訴求已經十分明顯了。本片的選材實在獨特,然而在具體操作上卻因為過度的雜糅和直白的隱喻反而變得語焉不詳,這是很遺憾的,但從當下呈現香港城市的角度,影片還是顯得獨樹一幟。